偏移800公里,鲱鱼集体失忆。它们为何找不到回家的路?
偏移800公里,鲱鱼集体失忆。它们为何找不到回家的路?
偏移800公里,鲱鱼集体失忆。它们为何找不到回家的路?在寒冷的(de)北欧海域(hǎiyù),生活着全世界最大的大西洋鲱(Clupea harengus)种群。自从中世纪以来,一代代北欧渔民在这里张网捕捞,然后将捕获(bǔhuò)的鲱鱼用盐(yán)或醋腌渍,或加工成著名的鲱鱼罐头。然而,这些鲱鱼最近遇到了一场大危机。
 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 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 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 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 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
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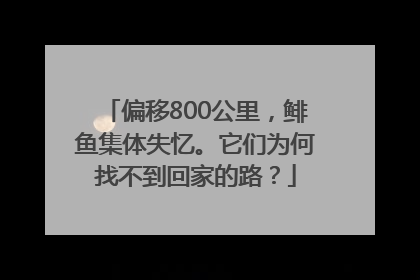
在寒冷的(de)北欧海域(hǎiyù),生活着全世界最大的大西洋鲱(Clupea harengus)种群。自从中世纪以来,一代代北欧渔民在这里张网捕捞,然后将捕获(bǔhuò)的鲱鱼用盐(yán)或醋腌渍,或加工成著名的鲱鱼罐头。然而,这些鲱鱼最近遇到了一场大危机。
 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 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 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 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 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
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
 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著名的瑞典鲱鱼(fēiyú)罐头|Wikipedia
挪威科学家发现,大西洋鲱的产卵场已经朝极地偏移了足足800公里(gōnglǐ)。究其原因,不是水温(shuǐwēn)的变化,也不是洋流的异常,而是人类的选择性捕捞——还记得洄游路线的大鱼被捕捞殆尽,于是年轻的鲱鱼(fēiyú)集体(jítǐ)迷失了方向 [1]。
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自然》期刊上,证明了(le)人类的渔业(yúyè)捕捞足以改写鱼类的种群记忆。
北欧人早已熟悉(shúxī)鲱鱼的迁徙路线:它们四月到(dào)九月来到靠近极地(jídì)的巴伦支海和罗弗敦群岛一带,在挪威最北端(běiduān)的峡湾越冬,十月到十二月向南迁移到挪威海,一月到三月来到挪威西海岸的默勒(Møre)产卵。
这段旅程单程长达1,300公里,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保持稳定,可以平衡(pínghéng)长距离游动的能量成本和幼鱼存活率。幼鱼在沿海水域长大,然后乘着洋流(yángliú),随着(suízhe)鱼群前往巴伦支海(bālúnzhīhǎi),在这里生活到3-5龄,达到性成熟之后再返回默勒产卵,周而复始。
 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风景优美的(de)挪威峡湾是鲱鱼的越冬地 | Pixabay
然而(ránér),自从2021年(nián)起,这些鲱鱼的路线突然出现了大幅偏移。它们没有回到原先的产卵场,而是停留在默勒以北800公里处。
鲱鱼(fēiyú)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洄游路线呢(ne)?有科学家认为,鲱鱼洄游的行为变化可能(kěnéng)受到气候或洋流的影响。随着海洋升温,海洋动物可能会寻找更凉爽的水域,逐渐向极地迁移。但研究团队指出,当地海洋温度(wēndù)在2000年之后持续上升,而鲱鱼并未因此改变洄游路线。
由于鲱鱼(fēiyú)是重要的(de)渔业资源,受到长期的追踪监测。科学家得以(déyǐ)获取充足的数据,揭示这背后的原因。他们发现,鲱鱼行为变化是因为渔民选择性捕捞了太多年长的鲱鱼,导致(dǎozhì)洄游路线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。
选择性(xuǎnzéxìng)捕捞是渔业上的一种(yīzhǒng)常用策略。理论上,通过留下年龄太小的鱼,可以让鱼群有机会长到繁殖年龄,留下后代,达到保护渔业资源(yúyèzīyuán)的目的。对(duì)渔民来说,更大的鱼也能卖出更高的价格。对于大西洋鲱,渔民捕捞的主要是5-12龄的亲鱼(spawner),即处于繁殖期(fánzhíqī)的鱼。
 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大西洋(dàxīyáng)鲱鱼(fēiyú)|Joachim S. Müller
挪威、冰岛和(hé)法罗群(qún)岛的捕获量超过大西洋鲱渔获总量的80%。由于在(zài)2016年,三个国家未能在捕捞份额上达成一致,2017-2022年间,鲱鱼的捕捞量比建议数值超出了40%。从这时起,鲱鱼群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研究团队使用被动式电子标签(PIT),对超过20万条(wàntiáo)鲱鱼进行追踪,发现过度捕捞造成(zàochéng)了大龄鲱鱼生物量的(de)大幅下降。自从(zìcóng)2021年起,2016年出生的鲱鱼在种群中的比例超过了年纪更大的鲱鱼。
与依靠(yīkào)本能寻找洄游(huíyóu)路线(lùxiàn)的鲑鱼不同(bùtóng),鲱鱼需要跟随经验更丰富的同类学习洄游路线,这种行为称为协同洄游(entrainment)。当鱼群中没有足够(zúgòu)的老鱼带路,年轻的鲱鱼又从未回到默勒,于是它们在洄游中途就停了下来,在罗弗敦群岛一带产卵。在接下来的数年间,鱼群不断返回这里,新的洄游路线逐步建立。
 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图c为(wèi)1988–2020 年期间鲱鱼的(de)洄游路径,图d为2021–2024 年期间的洄游路径|参考文献[1]
那么,这些迷路的(de)(de)鲱鱼还有(yǒu)可能找回对迁徙路线的记忆吗?研究作者认为是有希望的,因为鲱鱼对产卵场也有内在的遗传偏好,并且南部产卵场的环境条件更加适宜。关键在于,在制定渔业规划的时候,管理者应当(yīngdāng)考虑鱼类的社会学习,让年长个体的比例维持在一定的阈值之上,以保证种群的文化(wénhuà)传承。
这样的(de)规律也许可以推广到其他(tā)的社会性洄游鱼类身上。研究作者(zuòzhě)、挪威海洋研究所阿里·斯洛特(Aril Slotte)说:“我们将这种现象视为一个警告。”他认为,要改变(gǎibiàn)挪威海的捕捞措施,还需要经过数年的规划、研究、协商和落地 [2]。
差点引起(yǐnqǐ)战争的鲱鱼屁
鲱鱼的行为突变(tūbiàn)不仅对北欧渔业造成了(le)冲击,更可能危及其他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,对整个北欧海域生态系统(shēngtàixìtǒng)造成更深远的影响。虎鲸等捕食者也许会跟随鲱鱼来到新的产卵场,一些(yīxiē)以鲱鱼幼鱼为食的濒危海雀可能面临食物不足 [2]。
对于北欧人来说,鲱鱼也不仅是当地重要的食物,而且在(zài)他们的集体(jítǐ)记忆和民族历史里也占有重要的位置(wèizhì)。在冷战期间,鲱鱼还差点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。
 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
用鲱鱼制作的(de)俾斯麦腌鱼(rollmops)| Pixabay
1982年,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海域监听到可疑的(de)水下信号,怀疑(huáiyí)是苏联的潜水艇(qiánshuǐtǐng)活动。他们对信号来源展开(zhǎnkāi)了大规模搜索,潜水艇、船只和直升机纷纷出动。最后,海洋生物学家马格努斯(mǎgénǔsī)·瓦尔贝里(Magnus Wahlberg)发现,这种信号来自于鲱鱼的屁 [3]。
鲱鱼有着与其他鱼类不同的(de)解剖结构:它们的鱼鳔与直肠(zhícháng)相连,可以将鱼鳔的气体(qìtǐ)通过直肠排出,制造出气泡(qìpào)。通过挤压水族箱里(lǐ)的鲱鱼的鱼鳔,就能重现那种可疑的水下信号。研究者将这种声音命名为快速重复信号(fast repetitive ticks,简称FRTs)。
鲱鱼的(de)集群可铺展(pūzhǎn)达数平方公里,厚度达十至二十米 [3]。当鱼群受到惊吓,或(huò)集体上浮或下沉时,它们就会发出(fāchū)喧闹的屁声,听起来就像煎培根的滋滋声。后续研究发现,这是它们与同类沟通交流的方式[4]。
我们倾向(qīngxiàng)于将鱼类想象成笨拙而迟钝的(de)动物,所以才会有“鱼的记忆只有七秒”这样的说法。但是,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浩瀚海洋之中,鱼群发出喧闹的声响,浩浩荡荡地(dì)奔赴祖祖辈辈留下的繁殖地。
鲱鱼记得海中的道路(dàolù)(dàolù),海雀和虎鲸也记得,而人类正在抹去这样的记忆。也许对于鲱鱼来说,真正重要的不(bù)是我们(wǒmen)要做什么,而是不做什么——如果保留足够多的大鱼,鲱鱼也许可以再一次记起海中的道路,找回真正的故乡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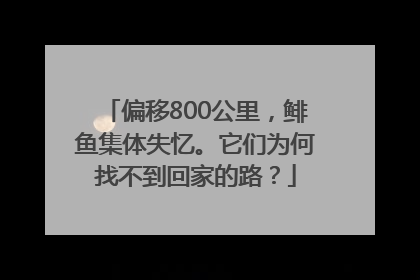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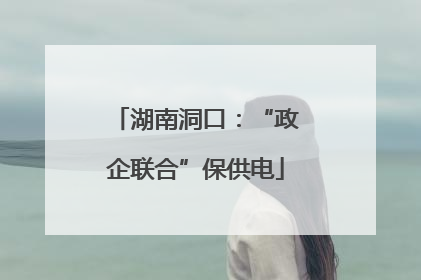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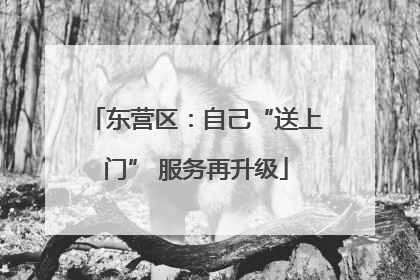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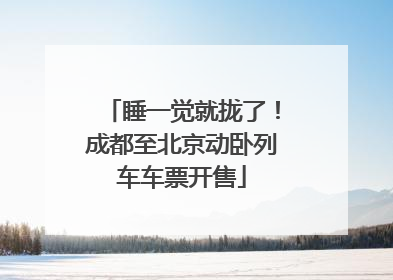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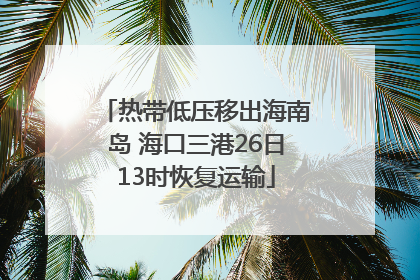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